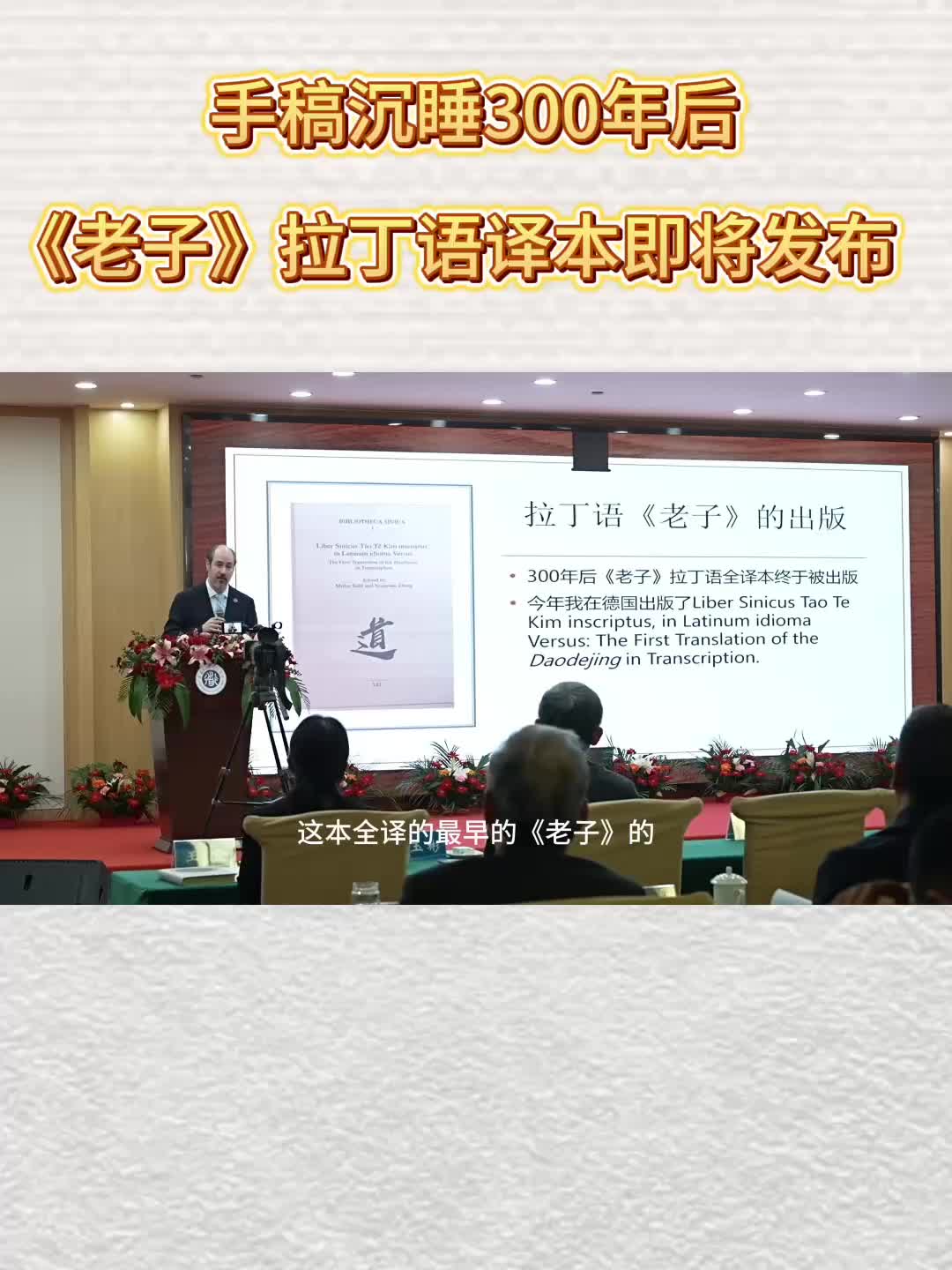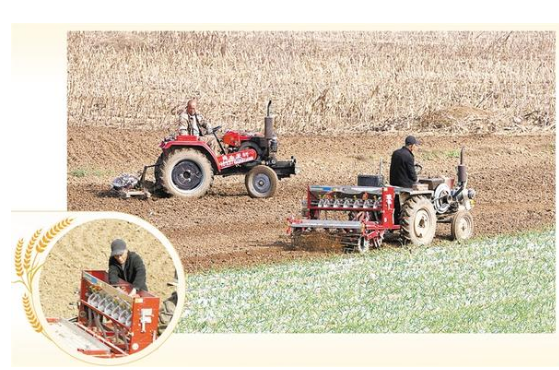記錄時代 逐夢三川

王晨(左)和母親看獲獎證書。

王永劍伏案趕稿。

杜營營(左三)、何晴在高鐵周口東站采訪。

田亞楠深入基層一線采訪。
編者按
記者節,是回望,更是出發。在這個屬于“見證”的日子里,我們讓記者走到臺前,分享他們采訪本中那些與城鄉發展同頻共振的故事。
從周口港的第一聲汽笛,到高鐵站的如織人流;從高標準農田的科技新綠,到智能工廠的紡織新聲……這些敘事背后,是記者日復一日的奔赴與凝視。他們的筆墨,既記錄時代奔涌的浪潮,也描摹每一朵浪花的姿態;他們的鏡頭,既對準發展的里程碑,也聚焦那些平凡而閃耀的面容。
愿這些帶著泥土與溫度的文字,讓您看見新聞背后,一群人與一座城彼此成就的溫暖真相;讀懂他們的故事里,新聞人不變的初心。
我與母親的紡織記憶
●記者 王晨
我家案頭,珍藏著母親兩張泛黃的證書:一張是1982年的“省先進工作者”,另一張是1983年的“河南省紡織系統勞動模范”。它們背后,是周口棉紡織印染廠徹夜不息的機器轟鳴、紡錘飛轉,是一代產業工人用青春為“周口制造”寫下的鏗鏘注腳。母親總說,那時的周口紡織品,是“響當當”的。
成為周口日報要聞部記者后,我無數次走進新建的現代化廠房。初時,面對智能設備與無菌實驗室,我的采訪報道總覺得隔了一層,差些火候。直到一次次深入采訪,我才醒悟:我正在記錄的,是家鄉發展的脈動;是讓萬千周口人透過文字,見證家鄉從“規劃圖”到“實景畫”的蛻變;更是母親口中那“響當當”三字背后,穿越時光的時代重量。
記憶將我拉回童年。母親的手,指節粗大,布滿深淺不一的裂口。她看守的細紗機有上千個錠子,斷線必須秒速接上,慢一步便糾纏成團。她的眉發衣襟總是沾滿棉絮,每天巡回行走相當于數十公里,傍晚雙腿腫脹得連布鞋都穿不進去。那是“腳不沾地”的戰場,更是周口工業起步期最真實的剪影。
而今的車間早已換了模樣。幾百平方米的空間里,只有幾位身著整潔工裝的年輕人在操作面板前巡視。一排排智能紡紗機自動完成接頭、換筒,全程不見半點飛絮。中控室的大屏幕上,各類數據實時跳動,每道工序進度一目了然。母親熟悉的“擋車工”,如今只需輕點屏幕,便能調度多臺設備。昔日棉絮紛飛的車間,如今是數據流在無聲奔涌。
“我們早已超越‘紡紗’本身。”技術員的話語透著自信,“從一朵棉到一件衣,全產業鏈在園區內閉環完成。客戶在線下單,系統自動排產,傳統模式下百人的任務,現在一套智能系統即可勝任。”
我將現場視頻發給母親。良久,她回復:“這真是紡織廠?變化太大,媽跟不上時代了。”那晚,我指著畫面細細講解:“這是扶溝縣蘇友紡織科技有限公司,染紗、織造車間全是電子控制;這是商水縣紅綠藍紡織科技有限公司,白坯布進來,經過退卷、預縮、染色等工序,24小時就能成品出倉。咱周口這樣的紡織項目可不少呢!”
母親眼角笑紋舒展:“你這孩子,倒成了半個紡織通。”她輕聲感嘆,“我不是懷念從前的苦,是欣慰這時代變得太快、太好,好得超乎我們那代人的想象。”
“但周口紡織,‘響當當’的底色從未改變。”我們母女異口同聲。
這一刻我終于明白,周口紡織正告別汗水澆灌的年代,駛入智慧驅動的新紀元。而我何其有幸,能以筆墨為橋,連接母親的青春記憶與家鄉的產業新生,記錄下這份仍在續寫的榮光。
見證大河新章
●記者 王永劍
11月5日,周三,再過3天就是第26個中國記者節。在這深秋的沙潁河畔,小集作業區港池水色澄碧,碼頭平臺上第5臺岸邊集裝箱起重機正在組裝,堆場上6臺軌道吊也在通電調試……一切都在熟悉的節奏中悄然變化。
作為一名跑交通口的記者,這幾年我不斷穿行于港口、航道、高鐵等建設一線。特別是小集作業區——這個河南聚全省之力打造的“11246工程”龍頭項目,我幾乎每周都會來到施工現場,見證平地起大港,記錄周口從“經濟通道”向“通道經濟”的跨越歷程。
自2024年4月小集作業區開工以來,昔日的村落悄然退場,現代化大港拔地而起。我那厚厚的五本采訪筆記,就是這個河南省最大集裝箱碼頭的“成長日記”。
“能參與這樣的重大項目,我深感榮幸。在這里見證大港崛起,是我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!”周口港港機設備安裝現場負責人李磊對我說。這句話,也道出了我的心聲——這何嘗不是我記者生涯中最亮麗的一頁?
這幾年,周口港大跨步前進:江淮運河通航,周口從“淮河時代”邁入“長江時代”;豫晉兩地能源外貿物流企業鐘情的“周口方案”,打造了北煤南運的“周口樣板”;43條航線輻射全球,周口港實現“箱通世界”;吞吐量從千萬噸級躍升至五千萬噸級……每一個數字背后,都是周口人“向水圖強”的執著。
于我個人而言,這是采訪,也是成長,更是視野的拓寬。站在碼頭平臺上,我深切感受到周口港的脈搏——它不再只是內陸的“出海口”,更是聯通世界的“橋頭堡”。
交通是興國之要、強國之基。周口港,連接的不僅是東南沿海與中西部,更是周口的機遇與未來。周口正將區位優勢轉化為交通優勢,在新發展格局中實現更大作為。作為一名記者,我很榮幸能用筆記錄沙潁河這條“黃金水道”如何釋放出“黃金效益”。
年底將至,更多期待已在路上:賈魯河復航工程開工建設、小集集裝箱碼頭開港、航道升級完成、港口吞吐量攀登新高……如今的沙潁河畔,千帆競發,樞紐經濟正蓄勢成潮。而我,愿繼續以筆,記錄這座臨港新城的每一次潮涌、每一段征程。
方寸車票里的時代印記
●記者 杜營營
整理舊物時,一沓紅色火車票從箱底滑落,票面上“周口—安陽”“K402次”的字樣依稀可辨。它們是我求學之路的印記,承載著當年外出求知的渴望與歸鄉的急切。
成為記者的四年里,我無數次踏入周口火車站與高鐵周口東站。從初訪時的生疏到如今的熟稔,我漸漸讀懂,車票背后是家鄉交通與時代同頻的脈動。那些紅色硬紙板車票,藏著最真切的過往:當年我攥著它登上傍晚6時的綠皮火車,在“哐當”聲中搖晃6個小時,于凌晨抵達安陽的校園。車廂里的擁擠與泡面味,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如今采訪所見,早已換了天地。2013年12月,周口火車站新站房及站前廣場投入使用,成為漯阜鐵路最大的客運站。2019年12月1日,高鐵周口東站投入使用,如今已是銜接多條鐵路干線的樞紐。截至今年7月7日,該站累計發送旅客超194萬人次。時速350公里的高鐵,將周口至鄭州的行程縮短至50多分鐘,比過去快了近兩個小時。車站里,智能安檢與實時調度系統高效運轉,伏羲、老子文化浮雕訴說著地域底蘊,免費充電設備等更讓旅途多了一份暖意。
漯阜鐵路公司周口乘務車間的列車員高明,是我采訪中結識的老友。16年乘務生涯里,他背過殘疾人、幫過急病旅客,也見證著鐵路變遷:“車次由少變多,速度由慢到快,但我們列車員服務旅客的初心始終沒變。”高鐵安檢值班員單鵬飛的話,則點出了更深的意義:“高鐵,是周口的一扇窗,讓更多人走進來,也讓更多人走出去。”
采訪結束后,我在高鐵周口東站與曾騎車送我趕火車的母親視頻通話。電話那頭,她一再讓我拉近鏡頭,聲音里滿是驚嘆:“這候車廳比當年的老站大十倍都不止,還有充電設備?以后出門再也不用帶充電寶了。”我笑著說:“等平漯周高鐵通車,去平頂山吃饸饹面,當天就能返回。您之前說想去北京看天安門,以后咱們周末就能出發。”
母親沉默了幾秒,輕聲說:“當年你上學,我送你到車站,看著綠皮車慢慢開遠,心里總揪著。現在車快了,車站好了,你們出門,我也更安心了。”
掛了電話,望著采訪本上“194萬旅客”“350公里時速”的字樣,我明白:從紅色車票到藍色車票,再到如今刷身份證即可進出站,這些變化不僅是交通的飛躍,更是無數周口人“走出去”的渴望與“盼歸來”的安心。而我能以記者身份,記錄下這份“快與暖”,便是最珍貴的職業饋贈。
采訪本里的農業“進化史”
●記者 田亞楠
11月4日,我站在商水縣張莊鎮南陵村的田埂上,眼前是2000多畝高標準農田。蹲下身,我翻開2022年初的采訪本。頁角卷曲,一段潦草的筆記躍入眼簾,那是我對村民老李的采訪記錄:“澆地要排隊2天,噴灑農藥全靠人工。”
那時我剛跑農業口,南陵村還延續著千百年來的耕種節奏。陽光下,老李和鄉親們扛著鐵鍬巡田,一畝地要忙活大半天。他抹著汗對我說:“種地苦啊,年輕人都不愿回來了。”
而此刻,同一片田野上,老李的兒子正通過手機APP控制著水肥一體機。無人機掠過田地,飛過的軌跡凝結為一行行數據,實時顯示在平板電腦上。
這4年,我的采訪足跡,恰如一部周口農業的“進化史”。
還記得第一次提起高標準農田建設時,許多老鄉圍著我好奇地問:“啥叫高標準?”我比畫著解釋:田成方、路成網、渠相連、旱能澆、澇能排。他們眼神里半是期待半是疑惑。
如今再次走訪,老鄉們反而成了我的老師。鄲城縣種糧大戶劉勇盛拉著我看他的“指揮中心”——一部手機,掌控千畝良田。“你看,點一下就開始灌溉,土壤濕度自動調節。”他滑動屏幕,氣象數據、蟲情監測、長勢分析,一目了然。
深入基層的這些年,我見證了無數這樣的轉變。西華縣的果蔬大棚里,物聯網系統自動調節溫濕度;扶溝縣的田間地頭,農技專家通過視頻為農民遠程診斷。我的筆下,不再只是春種秋收的傳統故事,更多了科技賦能農業的鮮活案例。
作為這場農業變革的記錄者,我的角色也在悄然轉變——從單純的旁觀報道,到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。我走進田間課堂,用鏡頭與筆桿幫老農觸摸新技術;我奔赴助農一線,讓“沉睡”的農產品躍上城市的餐桌。
翻過一頁頁泛黃的采訪本,看著眼前一架架飛翔的無人機,我深深體會到記者這個職業的獨特價值——我們不僅是時代的記錄者,更是變遷的參與者和見證者。
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創新、每一分收獲,都被我們的筆和鏡頭定格成永恒。當千畝良田在“云端”起舞,當古老的土地煥發新的生機,我知道,我和我的采訪對象們都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蛻變。
從泥土到“云端”,變的只是方式,不變的是周口人在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精神,以及我們新聞人始終如一的守望。